目录
1,鲍沟镇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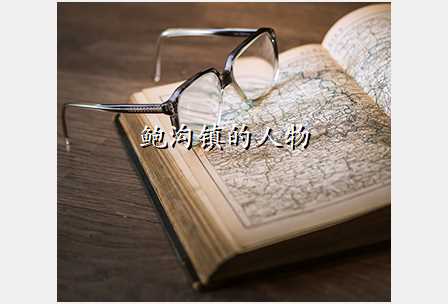
书画界名人:王学仲、马世晓、闵荫南,鲍沟镇是三位书画大家故乡王学仲1925年10月生于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宁家村,原名王黾,字黾子,笔名夜泊,号滕固词人,晚号黾翁,室名泼墨斋。书画家、教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天津书法家协会主席。1953年起在天津大学任教,创立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兼任南开大学、广州美院及日本筑波大学客座教授,王学仲艺术研究所荣誉所长,中国文联第八届、九届全委会荣誉委员,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画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精通书法、绘画、文学、哲学;是一位宏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家,创立“黾学”学派。一代大家王学仲先生于2013年10月8日晨7:17在天津武警总医院病逝,享年88周岁。1942年考入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曾师从邱石冥、吴镜汀、容庚,1945年毕业后由北平国立艺专墨画科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年画及油画,同时也接受齐白石、黄宾虹、张伯英、徐悲鸿、李可染等人的指导,书法功底深厚,诸体皆善,尤长于行草书,豪放雄健,跌宕多姿,绘画则以山水为主,精于书画理论,著述甚丰,1953年在天津大学任美术课教师。1978年入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创作。1985年天津大学建成“王学仲艺术研究所”,任该所所长。1989年获天津市鲁迅文艺大奖,出版有:《书法举要》、《中国画学谱》、《王学仲美术论》、《王学仲书法论》、《王学仲书画诗文集》、《夜泊画集》等。王学仲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总结出了三则治学主张,即:二言——欧风汉骨,东学西行;四感——文化的厚重感,历史的沧桑感,诗人的苍凉感,艺术的高贵感;四我——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作品还有《四季繁荣图》、《垂杨饮马图 》、《双鲤图》等。马世晓1934年出生于山东滕州鲍沟镇马口村,童年迁居徐州。幼承家训,笃志翰墨。1960年毕业于原浙江农业大学(今浙江大学)茶学系,留校任教。现为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江苏省徐州市艺术馆名誉馆长、浙江省高校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浙江省钱江书画院名誉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顾问等职。长期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教育工作。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二届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2013年1月30日,马世晓与世长辞。闵荫南谱名繁榕,别署逸文,以字行,室名芦花别馆,1939年出生于滕州市鲍沟镇闵楼村。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新疆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新疆书法家协会顾问(原新疆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新疆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军旅书画院名誉院长。幼承家学.五十年代就读于山东曲阜师范,师从著名书画家孔端甫先生. 其书法初沉酣于二王、唐楷,复浸淫于六朝碑版与汉隶奏简之间,然后上溯金文、羯鼓。40余年潜心书艺,转益多师,未尝稍怠,书风渐趋深沉简远。书法之外,兼涉文史、美学、国画、诗词写作与书画评论。 闵荫南书法作品曾入选全国第四届和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四届艺术节书法展览,中国首届书法艺术节(天津)等书法展、自治区成立四十年大庆书法展等书法大展中,五次获一等奖。1996年自治区文联授予“德艺双馨”称号。
2,关于王学仲作文
拜见王学仲先生的那天,天不作美,从北京出发就阴沉沉的,到了天津,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和摄影师浑身湿漉漉地琢磨着:这天气王老怕是不会出门了,可能会安排身边的人接待。出站,乘车,好不容易站在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馆门前的时候,已经比约见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令我们料想不到的是,屋内,端坐在木椅上看书的王老拄着拐杖欣喜地迎接。连同老伴,一起已经等了我们三十多分钟。
闻春燕:王老,您好!实在是很抱歉,我们来晚了。这么大雨,您是怎么过来的?
王学仲:你看见外面的三轮车没有,是老伴把我“蹬”过来的。
(王老的幽默让我们发笑,同时又深感歉意:真不知道这么大的雨两位老人是怎么骑三轮车过来的。)
王学仲:是啊!我的腿脚不方便,那就是我的专车。一直都这样。
闻春燕:最近身体怎么样了?都在忙些什么?
王学仲:身体还可以,精神也比前一阵子好多了。我现在以创作为业,平时写写画画作为日常生活,同时搞一点学术研究。以前论文写得多一些,现在老了,写得就相对少了。
闻春燕:我很喜欢您的诗,还有山水画。
王学仲:我年轻的时候主攻书画、诗词,出了很多诗词的集子呢。有四言体、五言体,也有绝句,律诗也写。现在画山水画比较吃力,画得比较慢了,画花鸟画就能快一点。我想只要有时间就尽可能多画几张好画出来。我一直比较喜欢画山水,以前有机会出去旅游的时候总会登山涉水,看见了好的山水景色就想画。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媒体炒作,就只是埋头苦干。我知道你家在西安,你们那里的刘自犊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一起开会,他从外表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书法家,没有架子,个子不高,还有点小罗锅;还有钟明善,书法理论上的造诣也是很高的,他写了《中国书法史》,还有其他很多著作,非常有素养。他们都是埋头苦干的人。
闻春燕:您老今年高寿八十一了,仔细算算,从五岁写字,六岁画画到专门从事书画事业,至今已经有七十五、六年了,您用了一生的时间在从事书画之道。很小就开始从艺之路,应该与您的家世有关吧?
王学仲:是啊,是与我的家世有关。我出生后,父亲就从《诗经》“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中取“黾”作了我的“字”。这个字成了我入世的先兆,即我生来无才,全靠勤勉努力,勤以补拙。我习书很早,也源于家学。我家祖籍山东临沂琅琊。据《滕阳王氏宗谱》记载,我们王氏家族为西晋琅琊王氏望族之后,王羲之一支渡江南迁后,另一支则散居山东、山西。王家先祖自元代迁至滕县郭河店后,仍然传琅琊王氏注重书道的遗风,以书法作为是否琅琊真传的标志。王家子弟不善写字,会觉得有辱先祖风范。我习画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受家族表兄的影响,他长我二十多岁,擅画兰竹,也常教我画画,我很痴迷,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兴趣。
闻春燕:古今中外学术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学派是激活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学派本身发育发展的基点,可是近年来学派缺失,理论界缺乏理性批判精神,阻碍了学术的自身发展。您创建的“黾学学派”,是以中国书画特别是以现代文人画为核心的一家之言,有人说,黾学的浮现与被认识定能对当今“有家无派,有派无学”的学术界,特别是书画界起到催化裂变的作用,但是这个学派似乎并没有被更多的人了解,是这样吗?
王学仲:我创立的黾学是一个立体综合的学说体系,其中包括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两个方面,哲学、诗歌、小说、书法、绘画等诸多艺术种类都包括在内。黾学中哲学的中心思想是蔽明论与归衡说。欲明则蔽,以蔽释明,任何科学家、政治家的学说政言都绕着弯阐述,不能浅白地说,哲学及众多思想亦然,借托他物以言之,否则不成为科学理论:“天意显示高轮回与天之高速运转,人的思力不接近时即以归衡的尺度重归旧章”。就好比两个人发生争执,结果总要以一方胜、败或两方和平求得结局,归于平衡,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在其中我提出的物识特性是被中西哲学家一直忽视的问题。我在哲学著作《黾子》中分述了天道、物道、人道、神道篇,讲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如何建立和谐的关系:作为人类,应该尊生爱物,面对自然也好,社会也好,要给予,而不是过多苛求;对于整个世界,应该怀有一种民胞物予的情怀,建立一个充满爱心的奉献的美好社会。
闻春燕:现如今,大家都在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足以证明您的学术理论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了。您的著述很多,尤其是您著作的《书法举要》详细讲解了怎么进画道、怎么进书道,让入门者学有所宗。
王学仲:是的。我的《书法举要》主要是介绍书法学的一个体系,归纳书法学为一个学术体系。以前书法就是写字,我把它统一归为书法,然后分门别类,加以评论整理,还有每种字体渊源、写法。这本书还要再版。我还写有两个姊妹篇:一个是关于书法的,另一个就是关于国画的,都要再版。这说明大家还是很认可。
闻春燕:您在书法创作方面建树卓越,您的创作心得对于后来者一定会起到强烈的教化作用。
王学仲:我很希望自己的创作心得能给别人一些启发。我认为学书法的人一定要勤奋好学,有较强的创新意识,有一定的学术建树。我在写字上的追求是:一字一翻新。每篇都有自己的面目,不重复。我经常会写一些新诗,记录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然后将这些诗用书法表现。我既然干这行,就力争写一首诗就写自己创作的。就算是写古人的诗,也会注明我摘录了谁的,必需有所遵循。一个书法家,一定要有文学素养、懂诗词、懂传统文化,否则你怎么能做书法家?王羲之的档次就在《兰亭序》上,可以边喝酒边作诗,有文学素养。现在的书法家行吗?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要求每一个人,很多人根本做不到。我不能自居有名,至少我不辜负这一行。
闻春燕: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画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中国画原本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记得您说过,中国文化是雅文化,中国书画不能破雅,以自然美为基础,但不是俗文化。现在我们国家是“全民皆书,全民皆画”,所以自然有一些人走向了俗文化。
王学仲:是啊,原来有一些人是搞高雅艺术,一些人搞通俗艺术,现在是乱套了,没有几个人愿意潜心研究高雅艺术了,因为没有钱赚啊,因为很孤独啊。就拿黄宾虹来讲,他的作品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但就其民族基因来讲,他所吸收的传统文化的精华的高度、深度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所以他的作品雅文化的成分比较多,雅文化的东西多了,被接受的范围就小了,以至于他的作品在当时根本无人理睬,甚至被贬低,直到很多年以后才逐渐被人理解和接受。
闻春燕:我们刚才说到“雅化”,那么怎样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的书画作品“雅”起来?
王学仲:就像你刚才所说的,现在搞书画的人很多,不少人属于附庸风雅之流。诗、书、画是滋养雅文化的源头,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画国画、学书法的人,都能写诗、填词、作赋,但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每一个从事书画创作的人的必修课。要懂得中国画的基本是什么,怎么把中国画立起来,第一是要会书法,第二是要懂中国古典文学。当然,我并不是主张中国文化返祖,再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中国画也要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
闻春燕:您提到外来文化,现在有不少人在探索西方艺术与中国画的结合,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画才会得到发展,才会有前途。您的看法呢?
王学仲:这种说法太片面。西方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可比性的。这就像有些人说“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是一样的,根本没有可比性。我们的高度外国人永远达不到,外国的高度我们也达不到,因为互相间的血脉不一样。再说中国画和西洋画的基础是不同的,造就的画家当然不同。现在的艺术院校普遍都是以西画为主,素描成为一切绘画的基础,虽然这也是必要的,但是素描再好,丢掉传统、不懂得“创造意境”,对一个国画家的艺术创作来说也是南辕北辙的。如果丢弃中国传统文化,一味在西方艺术中探寻中国画的出路,那一定是没有前途的。
闻春燕:您在1985年提出“现代文人画”的概念,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近年来,江浙一带出现的“新文人画”发展很快,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现在有几十个人在从事“新文人画”的创作,并且在国内取得了一定影响。那么以您为代表的“现代文人画”与“新文人画”的区别在哪里呢?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
王学仲:我首先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画家。因此我的画被普遍认为是学者画、文人画。但我以为,我的中国画应定义为现代文人画更为准确。现代文人画没有形成派,只是我的一个理论。为什么我要一定要称之为“现代文人画”呢?我们是现代的,跟古代讲的是不一样的。
我提出的“现代文人画”与“新文人画”也截然不同,现代文人画需要高修养、深功力、好人品,三者并重方可为之,而非一味标榜“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只知追求小情趣的无学之辈所为。我倡导的现代文人画是文人之时代性作品。我的创作立足于传统,但时代使然,必当有所创新。因此,我的那些文人画作品中依然流露的是一个文人雅谑机趣的情致。
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画得不像、也不准确,干脆冠一个“美名”,叫“画不像”。古代就有个画家叫倪云林,他画不像,就是草草不求形似,所以有些现代人画不像就说“不求形似,是新文人画的特点”。作文人画的人首先要懂文,你不懂文辞怎么叫文人呢?文人画应该有文学品称、诗词素养文化素养的沉淀,不像一般的画没有生活积累,就直接拿笔画。他们里面的一些人,诗别说作了,念都念不下来,满口错别字,这怎么能画文人画?
我有一篇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个观点,是针对新文人画而写的。现在一些青年学子不愿意向真正的中国画进军,以为“文人画最方便了,画好就好,画差就差。你画得像,我画得不像,我是新文人画”。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实际是没有真正理解文人画的意思,只是在硬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闻春燕:仔细看过先生的作品,无论是诗、书、画、文,皆觉意境深远,细细品读,发现作品中充盈着那种文人的“士气”、“稚谑”、“超形”和“机趣”。您的黾学理论的最高审美理想是野逸美。在您的“现代文人画”作品中不少作品都体现出这一特点,谈到“野逸”画风,不懂的人往往会想到狂放、张扬,对于您作品中的“野逸”应怎样正确理解?
王学仲:谈到“野逸”,人们往往会想到黄徐,五代的黄筌,南唐的徐熙。他们因画风、境遇不同而被世人称为“徐黄体异”。徐熙画风野逸,没有濡染黄家的富贵气象。我的画风继承了徐熙野逸的风格,将中国画“荒寒索漠”的笔墨情怀寄于我的作品之中。我的作品更注重抒发个性,但不取霸悍纵横之气,不染沉郁苍凉、俗甜富贵之气。绘画如做人,我的绘画作品在洗尽尘俗后,与我的人格是相一致的。
闻春燕:您在创立黾学的同时,又提出经书学派。经书存世有千年之久了,是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但是一直被忽视,您提出这一论说,引起了理论界的轰动。作为书画传媒,我们也很想借此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而不光是理论界。
王学仲:好啊!中国有很多像摩崖写经书法这样宝贵的艺术财富,从古代的手写经开始就已经存在了。比如泰山经石裕,那种与山川合为一体的书法特别壮观,山东这种摩崖经书很多,我很喜欢。我一直认为在碑、帖之外,存在一个经书学派。经书存世一千多年,没有得到充分认知。我在《碑、帖、经书分三派论》中提到:经派书自成体系的原因主要是:一、石刻摩崖为使佛教不灭这个思想,由写经进而刻石成为大型摩崖;二是其书法由经生体转化为摩崖体;另外,它的书写阶层既不是帖学的贵族士大夫,也不是北碑乡土书家,而是一些写经生、僧人和佛教信士。如果把六朝经派书加以概括,其一是经生体,其二就好似摩崖体。无论是经生体还是摩崖体,在今天看来,既不属于帖学系,也不应属于碑学系,而应独列为经学系的书法,才可以名副其实,我们也应确立这一书学系统的研究。关于现代书法的缘起,我是从书法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提出的,在当时我认为是社会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闻春燕:我个人有点不太理解当下的“现代书法”“流行书风”,有人称其为“丑书”。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似乎更多的是书法形式。写的字没有人认识,给人感官的第一反应就是真难看,这就是书法吗?《兰亭序》中有几个字是很难认识的呢?当然了,我不是从事书法专业的,仅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书法作为传统文化,需要发扬光大,但是目前有几百万甚至近千万的人在写这种无法识别的书法,让我们从哪里着手开始发扬,要发扬什么呢?难道书法只能作为一种艺术门类,一种现实存在,实际上却开始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吗?近两年来,当我们面对各地收藏者同样的提问时,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曾经有人戏言:哦,这些字你看不懂啊?看不懂就对了,看懂了就不叫书法了。这种现象似乎在圈内的争议也是比较大的。
王学仲:中国书法的兴起变动每个时代都有,从最早的刻画文字开始,书法的明确定位一直没有,但是书风的变动很多,每个时代必有每个时代的书风。当前有许多人在探索新书风,这个时代的画家、书法家有这个时代的风格是必然的。
作为一个探索者,我还是持一个宽容态度。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探索,就像任何人无法阻挡水流的前进一样,即使在流动过程中出现了几个漩涡,这也都是正常的,最终还是要汇入大海的。
现在的中国书法的确是走向了一个怪圈,别说你们迷惑,很多从事书法研究的人都迷惑了。几乎每天都有媒体寄资料过来,一有展览就上报,都在拍卖,搞市场,到处都是“大家”。其实一看就知道是在炒作。就像中国社会一样,骗子很多,广告很多,究竟哪个是真哪个是伪,让观众眼花缭乱。现在的中国书法已经不再讲究什么渊源造诣,主要看他有没有路子,有没有钱,有没有政治后台。我希望各地收藏者不要相信这些,没什么意义。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些不会写字的人在书法界任要职,这样下去,势必会导致书法走向泛滥成灾。很多中青年书画家,在学术上没有什么造诣,但把自己的市场炒作得很好,出版了很多很精致的集子。我们那时候出的书,都是学术性著作,出版社给作者稿费。现在全民商业化了,给出版社付钱就可以出书,而且印得越来越漂亮。
闻春燕:外界一直有这样的说法:王学仲这个人跟社会有点脱节,是那种不随波逐流,只专注于自己的创作的人。我曾经在互联网上看到过有关您的很有趣的小典故,提到您好象很少出售自己的作品,对自己的作品很珍惜,远道的人慕名前来,希望收藏您的作品,您好象很爱惜的样子,一点都舍不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王学仲:主要是我的假字画太多,你到书画市场、拍卖会场看一看就知道了。不知道那些人能卖几个钱?如果投入这个怪圈,弄得你自己都不分真伪了。我很担心有人拿着我的字画出去临摹造假,去骗人,所以总有点舍不得给人,后来我就干脆不卖字了。真正了解我欣赏我的,我送他几幅都可以。
启功先生曾经说过,现在有一些书法家的错别字太多,如果辨别那些书法家作品的真伪,有错别字的一般是真品,没有的就是赝品。这简直就是一个最大的讽刺。为了避免叫人看出来错别字,有人就干脆写草书,觉得草书就可以混过去了。实际上写草书尤为难,草书是很严格的,还有一个《草诀歌》。写草书啊,只有王羲之草书才能称圣呢,是最难的。“龙蛇经笔转”,就是跟龙蛇一样乱转;“有点方为水”,有了点才能成为水。它区分得很严格,没练过的人就会乱写一气。过去农民工的盲流多,现在书法的盲流也多了。
闻春燕:我国去年的书画市场发展比较好,而且因为一些原因,好多商家开始转向书画投资。去年浙江民营企业老板在书画投资上就有上千个亿,但大量的收藏品都是假的或者粗制滥造的。大众艺术水准的提高必须有一个过程,同时也需要更多热心的、懂专业的人士去普及,去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艺术品是有价值的,有效避免盲目性。刚才您提到对于现在艺术市场的现状多少有些失望,这会不会影响您搞创作的情绪呢?
王学仲:我明白,艺术市场必须要经过一个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大家的鉴别力也需要逐步提高,那时一些没有内涵的作品自然就会被淘汰。以前丁(井文)老和华君武倡导成立一个国画创作组,把全国的书画名人聚集起来搞创作。凡是有名气的都调过去了,全国各地有好几十位画家。丁老提出名单给华君武,还给了社会人力资源部。那时有个鉴别,必须任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去。必须是些学有所成、真有正国画造诣的人。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与一些在社会上胡炒乱炒的画家区分开来,去粗存精。我当时在北京中国画创作组工作了两年。先是在友谊宾馆,后来就搬了。去了两年就不能再去了,因为有教学任务啊。后来也换了领导人,丁老和华君武就不主持了。我看到现在有人卖的作品都是我们那时候画的,不知道已经转了几次手了。
我不图市场竞争,所以艺术市场的混乱对我来说无所谓。一个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力量太小,所以一个人的力量没办法左右一个社会,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像丁老这样的艺术家就比较我行我素,很有鉴别力,我希望像他那样。
闻春燕:记得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新加坡书协主席谈到您时说“如今中国还有如此之清流人士”。经过一番了解,看了您的著述,我也很有同感。
王学仲:我一生从未追求过金钱名利。我喜研老庄,深知功名利禄不过是黄粱一梦。我也敬仰魏征,宁做当世之“清流”。我的书画从不进入市场,不去炒作,不主动迎合大众的品味,作书作画只为抒发我的文人情怀。我在《我画我画歌》中曾写到:“我画即我性,我写我所爱,牙慧不欲拾,凭人说好坏……”我曾连任三届中国书协副主席,当过天津美协副主席,天津书协主席等等,同时我也是联合国世界科教文卫组织专家组成员,获得世界和平文化大奖、鲁迅文艺奖以及国学大师荣誉等等。这都是社会各界对我学术方面的认可。我之清流绝非空谈。我把有限的积蓄都做了公益事业,在文艺界我是第一个带头关注下岗工人的,还向他们捐款;非典时,两位医生因救非典病人殉职,我向他们的孤儿捐款以完成学业。做人应该胸襟博大,怀慈悲之心。我虽然乐善好施,但我同家人始终过的是极为普通的生活。我仰慕魏晋之清淡贤士,崇尚屈原、嵇康、陶潜之风骨,他们性情高雅而静默。我现已暮年,犹以淡泊之心,面对纷繁世事,唯有孜孜治学而笔耕不辍。
闻春燕:您在美院的十年间学的是中国画、油画,到天津大学的工作也是以绘画创作为主,但您在书法界的影响很大,而您对自己的评价却是“诗第一”,外界的评价出现频率最多的则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著名诗文书画家”。对于这些评价,您认为哪一个比较准确呢?
王学仲:给你说实在的,只能说他们是各抒己见,你很难要求媒体对你作出很公正的评价。媒体对我都是褒多贬少,有人说我的画好,有人说我的字好,有人说我的文章好,诗词好,很难有全面的评价,所以那一个作者写得准确我也说不出来。不管怎样,全部留给后人评说吧。
闻春燕:王老,今天能见到您并且聊这么多,我们感到很荣幸。您老一定要保重身体,我们有时间一定再来看您。
采访手记:王学仲先生曾经三度求学于美术院校,十年间曾经先后师从吴镜汀、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徐悲鸿、李可染等大师,转益多师使他得到了常人难以得到的心得。当年徐悲鸿先生独具慧眼,认为王学仲将来必成大才。王老没有辜负恩师徐悲鸿先生的期望,创建了黾学学派、经书学派,对于对继承、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丰富发展我国的书画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但如此,他热心捐助,没有丝毫迟疑,又展示了他仁爱的胸怀。
拄着拐杖,扫视着艺术馆展柜里那一本本已经被薄尘覆盖的书法论著和诗词集册,我们读到王老深邃的目光中对艺术永无止休的渴望,而在这渴望的目光中,又有着多少的不甘心?
出门的那一刻,我们不禁又看了一眼那架锈迹斑斑的三轮车。
人书俱老。先生,您已经达到了。
